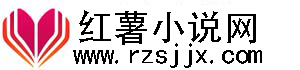100-110(5/34)
都不及元娘催促,窦老员外瞳孔骤然睁大,如遭定住一息后,抬起头就急切迈大步朝里走,似风一般冲进去,完全看不出老迈,更与他平日附庸风雅慢腾腾的模样截然相反。这么多年,他不知多少回梦见当日,停滞在阮家门外不敢进,半夜里惊醒喘息,倘若后悔能凝成实质,怕是已有一江流水般深长不绝。
虽与今日阮大的死不相干,但这情形,他不知重想了多少回。
迈步无比利落,元娘都未反应过来,他已经快冲到灵前。
又骤然停住。
窦老员外先是拜了阮大的棺椁,紧接着,向于娘子跪下,他俯首再抬起时,已是满面泪痕,“我、我悔啊,是我害死了兄长,误了大郎和二娘,是我,我的罪过,皇天在上,要死也该是我!嫂嫂,是我对不住兄长,但我当年……实在是太怕了。
“我怕担事,怕那些人索了我的命,是我软弱怕死,对不住你,对不住哥哥,万般罪过,皆起自我!”
窦老员外老泪纵横,言语激动,捶胸顿足,大冬日的,额上却浮起汗珠,可见情绪何等激昂。
于娘子神色木然,她听着窦老员外说话,却像是神游天外。也是,一直以来支撑门庭的儿子死了,那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,从小就孝顺忠义,勤奋习武,做了武官,若是寿数长一些,也不知会如何有出息。
就这样忽而没了。
她说是心如死灰,被带走半条命也不为过。
良久,在窦老员外的忏悔声中,她平静得犹如从海面传来的声音响起,像是无悲无喜的死人,“上柱香吧。”
“是。”窦老员外用袖子擦了擦泪和额上的汗,起身去上香。
他上完后,于娘子毫无情绪的声音继续,“停下做什么,还有你兄长的香。”
窦老员外如遭雷击,他不敢置信,旋即,整个人几乎要跳起来,朝着阮家兄长牌位的方向走去,才抬起脚走了一步,就被自己绊倒,来不及捂住磕碰的腿,便迫不及待继续上前。
他点燃香,泪水不住的往外流,对着牌位复跪三次,行了大礼,每一次叩首都极为真心实意,他想端端正正地行礼,神色郑重,可不知为何,手就是止不住踌躇颤抖。
最后一拜时,他长伏在地,久久不起。
等香插入香炉,窦老员外重新站在棺椁前。
于娘子的声音了无生意,目光空洞虚无,“你兄长等这柱香十多年了。”
窦老员外这辈子都没有今日哭得多,他殷切追问,目含期待,“嫂嫂,你宽宥我了?”
于娘子避而不谈,她语气疲倦,只道:“万事,总该有个了结。”
“二娘是个好孩子,拦来拦去做什么,都做空,一切皆是命数。”
她的语气犹如看破俗世的僧侣,枯寂无波,像是什么都不在乎了,生死面前,所有怨恨都被看开。
原本是两个人在对话,而哭得几乎直不起身的窦二娘却忽而用手强撑着挺直脊梁,她仰面看着于娘子,咬着牙,目光灼灼,无比坚定。
“我要嫁给大郎。”
“他活,我嫁,他死,纵是牌位,我亦践诺,绝不变节!”
她神色昂然,一字一顿,皆铿锵有力。
窦二娘是外表看着极为柔弱的女子,符合士大夫臆想中闺阁女子的一切特质,举止娴雅,识礼端庄,外出戴着面衣,倘若无人陪伴,兴许连城门都走不到。
但她亦是人,有着脱离了儒家理学所推崇的女子该有的心气脾性,柔弱的面容表象是极为刚烈的性子。
倘若她决定了,便谁也无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