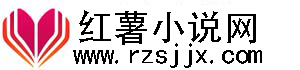第219章 母女争论不休(1/2)
厨房里,高压锅噗嗤噗嗤喷着白气,炖肉的香味弥漫开来。高冬雨正低头切着土豆丝,刀刃碰着砧板,发出细密规律的哒哒声,可那声音里总像缠着点别的心事,有点飘忽不定。“妈,”高小菲的声音从客厅传来,带着刚下班的疲惫,“饭快好了没?饿死了。”
“快了快了,”高冬雨应着,手上没停,“你洗洗手,准备端碗。”她顿了顿,那哒哒声慢了一拍,像是鼓点漏了一拍,“菲菲啊,今天…徐明那孩子的事,你也看见了吧?”
高小菲趿拉着拖鞋走进厨房,靠在门框上,眉头习惯性地微微蹙起:“看见了,那么大动静,整个医院怕都知道了。怎么了?”
高冬雨放下刀,转过身,拿起灶台边一个半旧的酱油瓶子,无意识地用抹布擦着瓶身上溅上的油点。她的眼神落在女儿脸上,又好像透过女儿看到了别处。“我是说…那孩子,徐明,”她声音低了些,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颤抖,“一个养子,为了他养父徐志超,能做到这份上……跪在咱们楼下那么久,替那个…替他爸负荆请罪,头磕得砰砰响,我看着,心口那块儿,真跟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似的。”
她停下擦瓶子的动作,手指用力地抠着瓶盖边缘微微发硬的塑料毛刺:“你说,这是什么样的心?什么样的情义?咱们…咱们是不是也该…也该好好想想?”
厨房里只有高压锅单调的喷气声。高小菲脸上的疲惫瞬间冻住了,嘴角一点点拉平、绷紧,眼神冷得像冰窟窿里捞出来的石头。她没说话,走过去,一把抓起高冬雨刚放下的菜刀,刀柄攥得死紧。她捞起案板上没切完的半个土豆,狠狠地、一下又一下地剁下去。
哐!哐!哐!
沉闷的撞击声在狭小的空间里炸开,震得人耳膜嗡嗡响。土豆块被粗暴地斩开、碾碎,汁液飞溅到旁边的抹布上。
“想想?”高小菲猛地停住刀,刀刃深深嵌进木砧板里。她扭过头,眼睛死死钉在母亲脸上,声音尖利得像刀刮玻璃,“妈!你让我想什么?想那个叫徐志超的?想那个在你怀着我的时候就卷了家里钱跑掉、让你大着肚子被他家里人指着鼻子骂‘不要脸’、最后像赶野狗一样把咱们扫地出门的‘好父亲’?!”她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棱,狠狠砸出来。
高冬雨被女儿眼中的恨意刺得一缩,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,后背抵住了冰冷的瓷砖墙面。手里那个酱油瓶攥得更紧了,塑料瓶身在她微微发抖的手掌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
“菲菲,妈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她艰难地开口,喉咙发干,“他…他年轻时候是混蛋,是畜生!他犯的错,老天爷都看着呢,他现在得了这个要命的病,躺在那里等死,这报应还不够大吗?咱们…咱们就不能看在…看在徐明那孩子一片赤诚的份上,看在他跪在那里替父赎罪的份上?人…人都快没了啊!”她说到后面,声音抖得厉害,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哭腔。
“报应?”高小菲嗤笑一声,那笑声又冷又硬,毫无温度。她“哐啷”一声把菜刀用力拍在沾满土豆泥的砧板上,震得旁边的碗碟叮当作响。“那叫活该!”她逼视着母亲,眼圈瞬间红了,不是委屈,是愤怒烧灼出的血丝,“妈!你心软,你善良,你记吃不记打!你忘了他家里人是怎么把咱们娘仨的东西扔到大街上的?你忘了咱们揣着那点可怜钱,像逃难一样扒火车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临海市?你忘了你一个人打三份工,累得晕倒在车间里?你忘了那些街坊邻居背地里戳咱们脊梁骨,说我们是‘被野男人甩了的破鞋’和‘没爹的野种’?!”
她越说越激动,胸脯剧烈地起伏着,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,烫在过往的伤疤上:“我发烧烧到四十度,你背着我走了三公里才找到个肯赊账的小诊所